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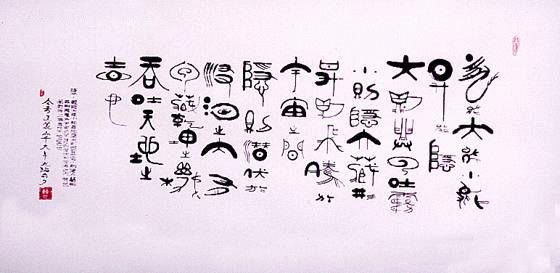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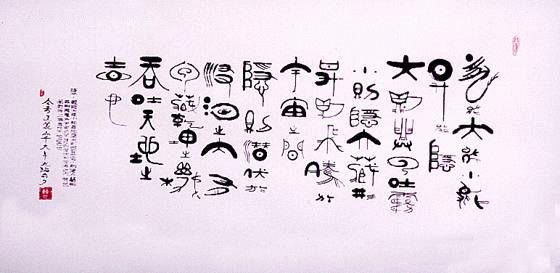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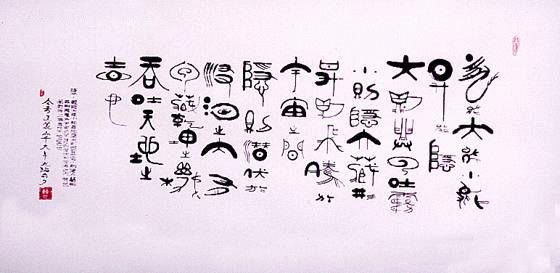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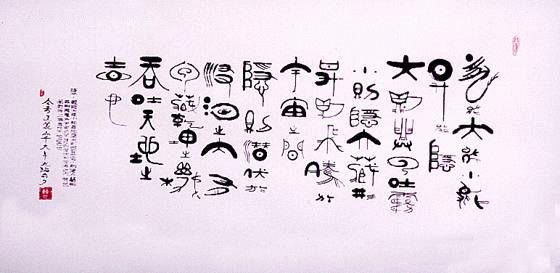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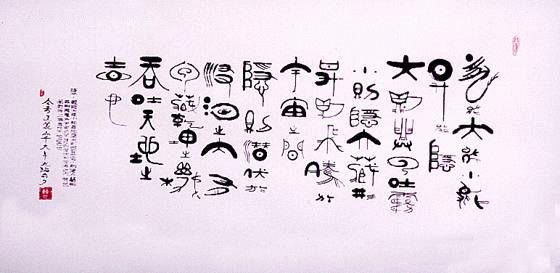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痞儿走运悲王朔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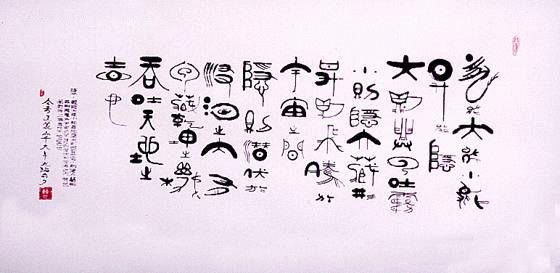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|
|
|
|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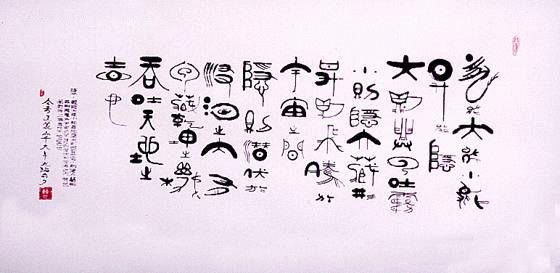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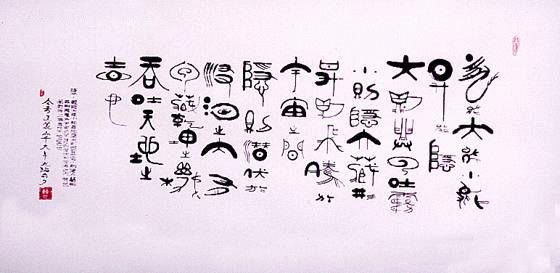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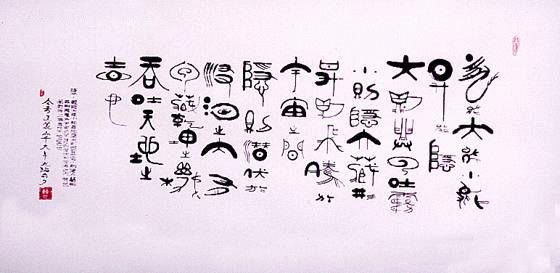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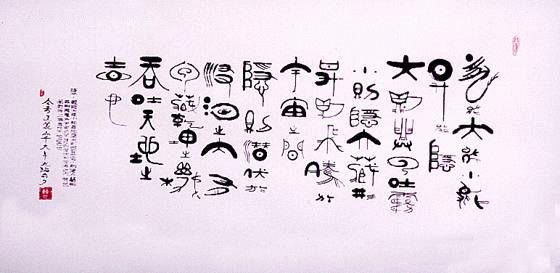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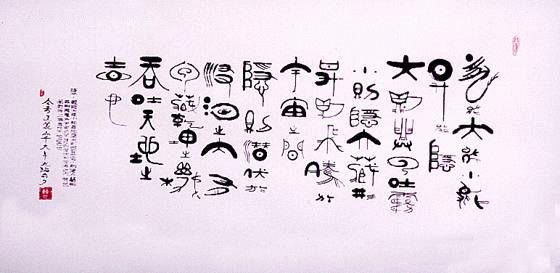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
|
笨猫 当前离线 OP海贼团船医兼宠物
|
绿色的是课本中没有的,剩下的大概都有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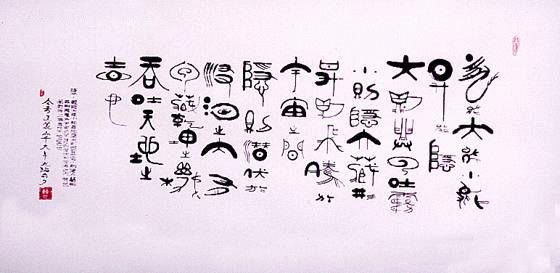 相思病,相思病,相思的人真他妈的有病。 |
||
Powered by Discuz! 7.2 Designed by Voora Island © 2001-2009 Comsenz Inc.
GMT+1, 2026-2-28 17:30.









